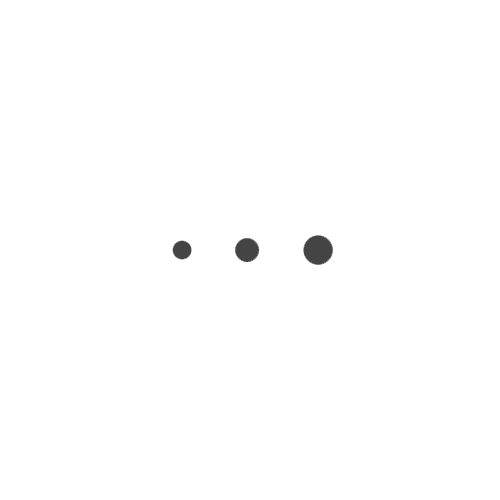(初撰於2013年)
近來風漸漸大了。
太陽滑落到山的另一端拉開了夜幕,今晚的夜空沒有月亮,星子綴亮了頭頂蒼穹的黑幕。記不清過了多少個夜晚,她日復一日地等待,緊掩的心扉被時間蒙上了一層厚重的塵埃,看不清底下赤紅的心,許久不曾啟用的青銅鎖染上斑斑鏽跡,鑰匙早不知道壓進哪一只木箱的箱底。四季的遞嬗在不知不覺間老去了她的年華,池塘裡的蓮花輪迴了好幾回開落,暖陽迎來了鳥鳴啁啾,又到這一季的花開,花有重開日,她等在季節裡的紅顏卻只能漸漸滄桑。
從前一大早,當天空還蒙著一層淺灰薄紗,透出若有似無的微微亮光,男孩就跨著竹馬來到女孩家門外吆喝。他帶著她遊戲,帶著她初看這個世界,草原、樹林、溪河哪裡都有他們的足跡、都有他們的笑語。兩小無猜的竹馬青梅彷彿仍在眼前嬉戲,稚嫩的童言童語還迴盪在耳畔,似乎昨日才覆了額的垂髫、將梳未梳的髮髻,轉瞬間就長及腰際,稚子雙雙長成了最青春的年華。
他們說書香門第的愛情是種病,輕啟薄唇,說什麼「不負如來不負卿」,可歎昨日才吟詠了的上邪,轉身卻輕易將它辜負。
「君既遠此行,求功且取名。所為是何故?染塵蔽誓盟。」成形的魚雁,在字裡行間裡難掩嗔怪,卻不想他游進你手中,相思的妒語太刺人,只願你記得最好的一面。
那早在七兮之時,便於吉日摘下的梅啊,在最嬌貴的時候珍藏,捨不得咬下一口,如今卻已臨發臭生霉。旅人遲遲未歸,青春華年在分秒的等待裡悄然斑駁。她的女工是一等一的好,在等待的時日裡縫製了從夏至到寒冬的衣裳,她要他不怕溽暑、不畏寒冷,那些衣裳層層疊疊塞進了她床頭的木箱,沒縫完的還有那麼多,可是箱子放不下了,這多到滿出木箱的衣裳全是為他縫的,一針一線裡盡是她的不捨跟思念,情緒也溢出了木箱,每天沖滌著自己,還有那同心結,她在每一件衣裳的心尖兒上都繡了同心結的模樣,包括他帶走的那一些,她說這樣他就不會忘了她。你問有沒有用?誰知道呢。大約就是女人安慰自己的一種蠱術罷了。
蝴蝶成雙、鳥兒成對,她手中開始褪色的同心結顯得那樣諷刺,像是在嘲弄這枯等的自己。望夫臺她不齒一顧,覺得那是人間最最癡傻的女人才成的模樣,她想她跟她們是不一樣的,然而她終還是成了一尊石像,端坐在面朝門扉的窗櫺,從此人生繡滿了等待。 「若明日你歸來,可還認得出我的長相?」她輕輕一聲嘆息,又有誰知道,知道她甘願至那長風沙,只願盼回那一襲青衣款款。她是如此心甘情願,用一場青春的等候,換一道眉間深鎖的憂愁,歲月篡改了紅顏,風華不再。
忽有一人身騎瘦馬,噠噠地踱至門扉,緩慢的馬蹄聲是被壓抑的急切,似害怕、又似期待。
「我必回來尋妳。若你還再等待我的歸期,就在門前掛上一株武陵吧。」
武陵花的花語是:愛情的好運。「願老天眷顧我們的愛情。」你說,而我知道,這是我們之間的密語。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跨坐馬背上,看著四周逐漸熟悉的景色,他忽然想起古人曾經說的這句話。
還在嗎?過了這些時日。時光走得太快,快到數亂了這是第幾個年月;又走得太慢,慢到鬢髮竟在不知不覺間染上絲絲白霜。還在嗎?還在等嗎?他急切地想要知道;卻又畏懼真相,害怕等到自己無法承受的悲傷結局。
更近了。離自己的願望、自己的夢想、自己這些年心心念念的心尖兒上那一顆朱砂痣。
他遠遠地盼。
「我必回來尋妳。若你還再等待我的歸期,就在門前掛上一株武陵吧。」他當年說的一句話,如今帶著泛黃的語調又在耳邊響起。
他遠遠地盼。
沒有。門前空無一物,乾淨的就像初生的犢子,沒有花、沒有葉、沒有枯萎或者茂盛的花開。甚麼都沒有。
他遠遠地盼。再怎樣迫切的眼神卻也盼不見門前的武陵花。
他騎著瘦馬緩緩離開,馬鳴蕭蕭、蹄聲噠噠,一步向前三次回頭,直到門扉融入身後模糊的景色。
噠噠馬蹄聲傳入院落,若有似無,像是從遙遠的天邊傳來,百年難得一聞的天籟,漾起她心底沉寂已久的波紋,「呀!」她驚呼一聲,疾步門邊,吐納幾口迫不及待的氣息,好容易鼓起勇氣,乍一推開門扉,滿懷希冀的神情急切切地張望。
「可是你回來了?」
卻見漫天揚塵,一人一馬的身影漸行遠去。
近來風漸漸大了。
她回首不見門前的武陵,俯身拾起掉落在腳邊的那一株掛回門扉,過客噠噠的馬蹄再激不起波瀾,她轉身離開將大門咿呀闔上。
又是一陣風,門扉上武陵花顫巍巍地在風中抵抗,終不敵吹襲墜落地面,粉色的花瓣沾染一身塵土,參雜進門前散落滿地的粉紅地毯,再分不開差異……
過客總是醉或夢著。
說書人嚥下一口羅漢果茶,這茶潤喉,是吩咐伙計特地熬的。他唰地一聲甩開摺扇,擺弄了兩下,扇起一陣微風拂涼了額上冒出的汗滴……
甚麼是紅色?你問。
紅色,是大囍、是大哀;一方是囍、一方是哀。
大紅色的禮服襯著新人,擋不住新娘眉眼的悠悠笑意;絳紅色的喜氣圈著新人,掩不住新郎眼底的殷殷期盼。 當初駕著瘦馬不捨地離開,再次隻身上京,武陵花逐漸枯碎成記憶裡一地隨風飄散的塵埃。終於今日大婚,似乎所有人世間汲汲營營的追求他都已經達成:事業有成、佳人在側。偶爾,只有在午夜夢迴時候,才踏著無聲氣息悄然入夢的那一株武陵,夢裡是漫天飛舞的粉嫩花瓣,還有繁盛茂密的桃樹林,大約是對遺憾的渴望吧。
而他當然不知道,在遠方的宅院裡,一盞掉落的燭燈燎起火舌,腥紅色的火舌漸漸壯大,當火舌終於舔上屋脊,她只是坐在屋裡靜靜地凝視,任由火勢恣意猖狂,耳邊是無情的劈啪火焰,她彷彿透過火焰看見喜慶的大紅鞭炮,在炮竹的頂端閃爍著火光,火光一耀燃起一片希望、劈啪聲震碎過去枯等的害怕。
火越大,心卻越涼,終於從灰燼裡燒出一株武陵花,不惹塵埃靜靜地在火中盛放,浴火的武陵花瓣簡直紅的要滴出血來,「我必回來尋妳。若你還再等待我的歸期,就在門前掛上一株武陵吧。」一匹馬、一雙人、滿山遍地盛放的桃花。是夢嗎? 「武陵也喚桃花,妳就是我的桃花,或白或粉或紅,都好看,真好看。」
是夢也好。她想,這樣也很好。
若問世間喜與悲,道不盡哀戚戚一句成多餘。
這世界悲歡離合,最終都不過化作說書人口中的一聲嘆息。
人走茶涼,說書人闔上紙扇,抿了一口早已失了溫度的羅漢果茶,面前幾排木桌上是狼藉的杯盤。說書人清清喉嚨,步至屏風後,屏風上繡了一隻開了屏的孔雀,用金線鍍了周身,已經開始灰黃的珍禽生生透出一股過時的霉味,卻依舊遮掩不了那一臉的傲氣。
說書人屈身彎上屏風後方的躺椅,不多時,傳出陣陣鼾聲,鼾聲合著窗外啁啾,繪出一幅春意暖人的晌午祥圖。
前頭夥計三三兩兩不停地來回忙碌,收杯拾盤、擦桌拭椅,屋外春色正好,陽光透過窗櫺斜灑進店內,在木桌上、板凳上、地面上灑成幾段金黃的碎夢,將整個屋子烘出暖洋洋的一片。
夢裡總有那麼一張笑靨,盛開在三月芳叢,笑起來的模樣清新又醉人。在燈火繁華處,她明媚如春的容顏鑲入唐宋詩詞,美眷激起陣陣漣漪。馬蹄噠噠,這一次沒有錯誤、沒有被風吹落的承諾、沒有誤以為的過客;跫音低低響起,歸人揭開鶯月的春帷、推啟緊掩的窗扉,滿屋蕭瑟躍入眼簾,屋子的女主人顫抖地瞅著自己,似驚似喜,眼底止不住湧出淚來,淚珠遊走在她一對汪汪的明眸,拉成一條晶瑩,啪的一聲跌碎在足尖的土地。
在庭院角落,有一樹武陵花繞著枝枒盛開。
大約是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