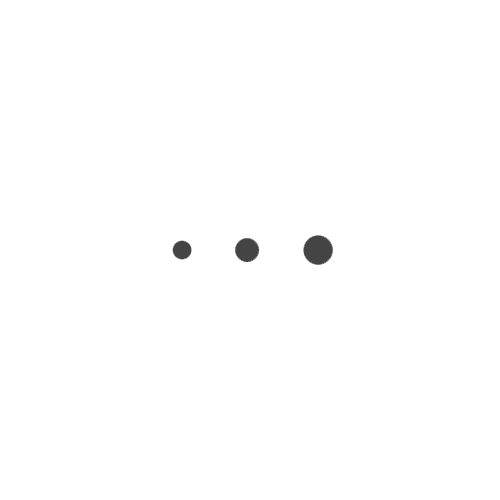段七
去的久了,也跟大家熟識,我漸漸地跟一個男學生好上了,他一開始其實很不待見我,覺得我只是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土包子,他後來告訴我,是我認真的態度改變了他的想法,他說我什麼不懂就問,也不在乎別人會不會嘲笑自己,他很佩服我的勇敢。他開始教我學習,只要哪裡不懂他就會耐心地說給我聽,每當這個時候,阿弟就在旁邊自顧自地玩耍,他只當我是因為家裡沒人,所以要帶著弟弟一起學習,自然從來沒想過阿弟是我丈夫。他也對阿弟好,阿弟很喜歡他。
因為他,我的學習生活多了一點淡淡的粉紅,但是我不能告訴任何人,連阿弟也不能,這是只屬於我的秘密。他帶我去看了很多地方,自然阿弟回回都跟著,阿弟的媽媽也沒有起過疑心。我知道他喜歡我,我也喜歡他,但是我們誰也沒有說破,他還是給我上課,給我教我不會的東西。我們享受這樣的曖昧,這種感覺特別好。
又過了五年,這一年阿弟的母親決定讓我跟阿弟「圓房」,我知道「圓房」是什麼,畢竟我也算是一個女學生,但是我不想,阿弟就像是我的親弟弟,我沒辦法想像,這實在太奇怪了。我不能拒絕,儘管我內心女學生的靈魂不斷呼喊叫囂著要我抵抗,但是我身為一個童養媳卻是不爭的事實,他們養我就是因為這一天,如果我不服,我看過因為不想「圓房」而抵抗的人,後果很慘,我好不容易在這個家裡過得很好,我沒有必要、也不想打破這個平衡。
我以為我的人生幾乎就要在這裡劃下終點了。跟阿弟圓房、不再去學習、生一個阿弟的兒子、帶兒子,最後慢慢地變老,或許再給阿弟的兒子買一個童養媳,就想阿弟的母那樣,他的母親也是童養媳,童養媳就像是一個無止盡的因果循環,沒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
就在這一年,一場戰爭改變我的人生。
那時候上海跟南京大學的學生主張著「反飢餓,反內戰」。《新華日報》每天登著中共軍隊勝利的戰報,又將中共俘虜的國軍公布在報紙上讓家屬認領。在節節敗退之後,蔣公最後終於決定退守台灣。阿弟的家人也整理了所有的行李要去台灣,原本預定的「圓房」也不了了之。「生活都有問題了,誰還管什麼圓不圓房啊!」阿弟的家人這樣說。他們本來不打算帶我去的,畢竟多一個人就要多一張船票,到台灣還不知道未來,多一個人等於就是多一個麻煩的包袱。「不行、不行,阿姊不一起去我就不去。」結果是阿弟的一句話救了我。我何德何能啊。「阿姊,妳就是我的阿姊,阿弟怎麼可能把阿姊一個人丟下來。」我才發現,原來我們的關係早就超越了阿弟父母親預想的童養媳跟小丈夫,而在不知不覺間昇華成更穩固的親情。
臺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以前的我,只從別人的對話裡聽說過幾次,他們都說台灣是一塊人們夢想中的淨土,沒有煩惱、沒有戰爭、所有人豐衣足食。「妳有聽過桃花源嗎?那裡就是一個十足的桃花源境地。」
我們打包好所有行囊,搭上船,隨著許多搶到船票的逃難的人一起,海上風雨飄搖,船在大海上像一個失去方向只能隨波逐流的落葉,但是再怎麼樣搖晃的船身,都遠沒有戰爭的中國讓我們害怕。「只要到了台灣,我們就安全了」,大概是這樣的信念堅持著我們這一群人。
終於到了岸邊,船上所有人爭先恐後地下船,人潮蜂擁向外擠,我原本緊握著阿弟的手在人潮推擠之中竟然空了──我跟阿弟他們一家人竟然在剛到台灣的瞬間就走散了。四周滿滿地都是人,我在人群中大聲的叫喊著阿弟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叫到嗓子都啞了。我想要站在原地等著阿弟他們家的人來尋我,可是後面不斷蜂擁的人群把我往前推,我的腳幾乎碰不到地板、幾乎是人群夾著我往前移動,我一個人的力量根本抵擋不了,只好順著人群,等到終於停下來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身在何方,更不用說回頭再去找阿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