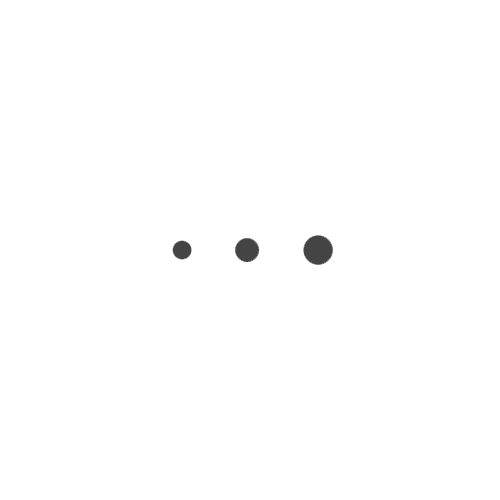段四
阿嬤軟綿綿地靠在沙發椅背上,目不轉睛直盯著她手裡的翡翠墜子,她的專注讓我訝異,「阿嬤……」
「央央,你聽過新婦仔嗎?」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一種婚姻的習俗,是將未成年的女孩送養或賣到另一個家庭,在另一個家庭裡長大,長大以後嫁給他們的兒子。這些女孩就被稱為「新婦仔」,江南地區則喚「童養媳」,雖然稱呼不同,說的其實是同樣的悲哀。
奶奶就是別人口中的「新婦仔」。
奶奶的老家在中國的農村,家裡特別窮,吃飽穿暖都是問題,偏偏那時候又遇上日本跟共軍交互的打擊,戰爭一場接著一場,這裡歇了那裡烽火又起,全不給人喘息的機會。
「你想聽故事嗎?」阿嬤把耳墜子遞給我,開始訴說一段那年深埋在厚重塵土之下、帶著火燒火燎味道的故事……
那是一個艷陽天,但是炙熱的太陽照不清我心中的陰霾,我斜躺在牛車上,任由酷熱的陽光打在身上,身旁是一個小包袱,裡面寥寥幾件破舊的衣服還有母親大早起來燒的幾塊餅。我的小小身子因為長期營養不良,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了兩歲,我隨著崎嶇的路面顛簸,小包也顫巍巍地抖顫。 我看過很多人在這個時候都會大哭,但是我偏不哭,沒有什麼好哭的,就當是搬了家、重新投了一次胎罷了。
我是家裡最長的女兒,下頭還有兩個弟弟,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我下田勞作的時候,五歲的弟弟也會陪著我一起幫忙,但僅有五歲的年幼孩童能幫些甚麼呢?弟弟們都不過還是嗷嗷待哺的年紀。說是幫忙還不如說是陪伴來的更為貼切。
從我記事以來,中國就一直在打仗,或者說是在被打,整個中國都是煙霧瀰漫,沉溺在一股戰爭的低氣壓之下。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無止盡的戰爭,反正國家的事情怎樣也落不到我頭上來,我那時每天最大的願望,不過就是能夠躺在屋內的通鋪好好睡上一場日上三竿的覺。
我還記得父親長滿厚繭的手足還有母親日漸消瘦的身軀,看著他們每天都為了生計煩惱、為了生活而深鎖的眉心,那時候跟我同一個村的女孩都被賣去做童養媳了,我想那大概也會是我的命運,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來。
當年母親將所有的財產換成了金子,「雖然現在的日子看似和平,我們還是過著平常的生活,該幹嘛就幹嘛,可是誰又說得準下一刻的事情?」 我站著,母親坐著。我這才發現,曾經是母親最引以為傲的烏亮青絲,現在變得滿是斑白;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母親的聲音變得如此嘶啞?我記憶中的母親,那個黃鶯出谷一般,時不時哼唱兩句的母親在不知不覺中在柴米油鹽的煩憂中消逝了。
「要是村子裡突然闖進來一輛裝甲車,還是有一堆人拿著步槍衝進來,那個時候我們連逃都來不及啊!」母親說,「等到了那種地步,錢幣、紙鈔的,哪裡還派得上用場?還不全成了廢物。倒不如換了金子,心裡踏實些。」
我看著母親的臉龐,母親的臉啊,曾經是那麼精緻細膩。小時候最喜歡摸著母親的臉,感受她細膩的皮膚,還有她滿滿的愛意,從笑彎了的眼睛跟嘴角裡溢出來。母親當初被街坊鄰居稱羨的一張臉,如今卻已經染上了風霜、染上歲月無情的痕跡,她的眼角深深地刻上無數條魚尾紋,還有眉間的皺紋,濃得化不開的擔憂全寫在她臉上,擔憂我們、擔憂戰爭、擔憂生活。我多麼希望能讓她的眉頭舒展開來,讓她再變回我記憶裡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