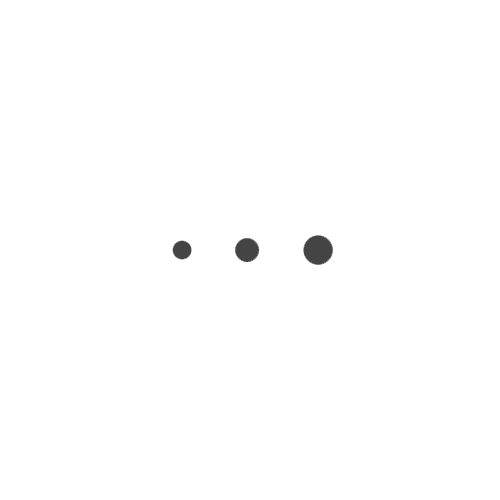(初撰於2013年、後修於2017年)
故事開始於高一軍訓課的作業。
作業主題是訪問家人與戰爭間的事,故事從我媽口裡聽來的,雛型是我外公,童養媳是外公的姊姊。
後來被我胡寫亂謅、加油添醋,改寫了兩次,成了現在(此篇)的樣貌。
段一
來到這個與世無爭的小城鎮已經兩年,這裡陽光常照,好似沒有四季的流轉,只有春天,春的日暖風和、春的鳥語花香、美好嬌媚。 大學畢業那一年,就像大多數的畢業學生一樣,前方的道路好像突然被蒙上了一件薄紗,我不知道要做些甚麼。「總是要找個工作吧。」夏倪茹透過臉書敲了一句話過來。
「嗯,我知道啊。」攪拌著電腦旁冒著熱氣的咖啡,我突然有點懷念學生時候無憂無慮的生活。
我的個性一直都是冷冰冰的,不會交際,也不會說好聽話,幾乎都是一個人獨來獨往,曾聽別人說我太冷了、不好親近,但我只是因為太久沒跟人群相處,漸漸失去了這個能力。
這樣不討好的個性,在我大學四年裡倒還有一個人陪著我。我跟夏倪茹從國中認識,不同的高中,卻又同一個大學,也不知道是我考高了,還是她考壞了,兜兜轉轉一圈又再次相遇,這應該就是老一輩人常說的「緣分」吧。但我們的交流方式也特別,不是轟轟烈烈、熱熱鬧鬧的那一種,通常就是坐在一塊,然後各做各的事情,是名副其實的「陪伴」。
「喂,阿央。」
「嗯?」我懶洋洋地翻閱手上的小說,是她最討厭的文學小說,夏倪茹戲稱的「假文青做作的不可或缺之物」。
她總是感嘆:「阿央阿,如果說這世界上還有誰是從頭徹尾的文青,那個人一定是妳。妳簡直……太文了!」她讀的是理科,國文一向很差,還記得國中時候,她的作文常常被老師拿來朗讀──作為警惕的錯誤示範。
她對著我的書翻了一個大大的白眼,「你說我們以後會變成什麼樣的人啊?我不想變成我爸爸那樣……」夏倪茹的爸爸是個酒鬼,其實如果僅是酒鬼那也罷了,偏偏她爸爸是會發酒瘋的那一種。
十三、四歲那幾年,我們都還只是沒見過世面的小鬼頭,卻又要學著大人裝扮自己,覺得那衣服太醜、那個包又太幼稚,挑三揀四的買,妝扮起來其實還是一樣的孩子氣。在那個將成熟未成熟的年代,夏倪茹已經經歷過她人生不知道的幾次的「與死神交臂而過」。夏倪茹的爸爸發起酒瘋,總結起來就是十二個字:鬼吼亂叫、遇人就打、逢物就摔。
夏倪茹身上總是舊傷未消,新傷就起,她每次對我哭訴,我只能靜靜地聽,我沒辦法告訴她「我懂、我明白」,因為我確實一點都不瞭解。我爸爸是滴酒不沾的,不是為了什麼神聖的理由,只是他酒量差,但為了保持他的男性尊嚴,他永遠都說「不行不行,喝酒壞事。」倒是引來爸爸那一群朋友的妻子讚嘆不已的目光。這讓他很驕傲。
「我想……我也不知道我想變成什麼樣的人,就是不要跟我爸爸一樣,太讓人害怕了。喔,我也不想跟我媽媽一樣,嫁給這種男人,這真是……太糟糕了。」夏倪茹說。其實髒話可以包含所有人類想表達的語氣,但她自詡一介淑女,我從沒聽她暴過粗口,偏偏她國文不好,說的都是最簡單的辭彙,大概因為這樣,她說話永遠都缺少了一股氣勢。
「妳呢?妳想變成什麼樣子的人?」
「嗯?」我翻開書的下一頁,剛好看到維特寫給夏綠蒂的最後一封信:
……我寫這封信給妳時,不帶浪漫的激昂,而是冷靜,在這一日之晨,今天我將最後一次見到妳……我只求一死……喔,上帝!祢將最苦澀的淚水當作最後的清泉賜給我……這並非絕望,而是對自己的決心深信不疑,我要把自己獻給妳……如果妳在一個美麗的夏夜爬上一座山,請想起我多常走上那座山谷,然後望向教堂墓園,再望向我的墳頭,風兒拂過夕暉映照在長長的草上,款款搖擺……我心意已決,多好啊……當一個人在對自己說:「這是最後一個早晨」時,這感覺無與倫比!卻也最接近晦暗不清的夢幻的感覺……能夠光榮地為妳而死,於我是幸福的……槍已上膛……
「我不知道,」這封信的內容讓我悲不可遏,「但是,如果可以的話,在生命最燦爛的時候死去,感覺也很美。」
「拜託妳不要再看奇怪的書了好不好。」她又翻了一個白眼,不過這次是對我翻的。「我才不想這麼早死呢,我想要在這個世界上一直行走,走到老、老到走不動。」
夏倪茹當時看著天空,那一天天氣其實不好,起了一場大霧,能見度很差,四周只有一片霧茫茫的慘白色,但是我卻從她眼中看見了蔚藍的浩瀚天空。
或許我們的未來就和這一片天空是一樣的,偶爾藍天、偶爾白雲、偶爾又一陣暴雨,沒有人知道他下一刻會成為什麼模樣,但或許就是這樣的不可預期性,漫漫人生長河裡才多了一絲樂趣,帶著一點壞的惡趣味。
那一年我們大一。
段二
「所以……你找到工作了嗎?」我傳過去一句話。
「不算吧,應該是先到我媽的公司幫忙,反正也不知道要做什麼,老是待在家裡窩著也不是辦法,就走一步是一步囉。」
「這樣啊……」
「你呢?現在有什麼打算?」
「……我想去鄉下住一陣子,住我阿嬤那裡。」
「阿央。」我可以想像當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會是什麼表情,肯定是無比沉重的語氣,輕蹙著眉頭,然後重重地嘆一口氣。「你知道嗎?逃走是不對的,這實在不是一個成熟的作為,身為一個二十多歲的成年人,我們應該要面對,然後解決。」
「你最近又看了甚麼書?」
「你怎麼知道我最近有看書?」
因為我了解夏倪茹,夏倪茹實在不是一個世故的人,說不出這些話,儘管這並不是多麼深奧的思想。
在我們畢業前夕,跟我交往了兩年的男朋友過世了,在我知道地當下我並沒有哭,好像淚腺突然斷掉了一樣,當時所有人都不敢跟我說話,認為我的靜默是極大的哀傷,貼心地留給我獨處的空間。 只有夏倪茹跟別人不一樣。她一言不發,走上前摟住我的肩頭,「徐央。」她在我耳邊低語,「妳還有我。」
我終於大哭了一場。
我告訴她,從此以後我再也不要交男朋友、再也不要跟誰要好了。所以她總說我只會一昧鴕鳥心態地逃避。
但我並不是逃走。我只是還需要一些時間沖淡這件事情、需要一些空間給我封存這段記憶。
就像是煮一壺水,當水沸騰的時候,因為到達沸點而蒸發的水蒸氣,會在打開水壺蓋的瞬間,一股腦兒爭先恐後地離開水壺頂端的狹小空間,都只是一種自然現象,你不能要求他們繼續待在壺口下的空間,就像我沒辦法在承受哀傷之餘,上緊發條在都市生活,這對我而言是相互違背的。所以我不是逃走。不過這些話,沒有必要讓她知道。
其實世界上有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沒有必要昭告天下,就算全世界都誤會你、就算全世界只有你支持自己,但我們終歸還有自己。
段三
奶奶住的三層樓高的透天厝立在馬路旁,自從她四個兒子各自成家,她就一個人住在這裡,奶奶說她喜歡鄉下的寧靜、喜歡鄉下的人情味、喜歡那種一出門就有人跟你噓寒問暖的親密。在馬路兩旁的居屋,雖然緊密地靠在一起,在鄰居感情緊密的同時又各自孤立、各自為國,雖然親密卻不會過度干擾,仍然可以保有自己的空間,跟都市的各掃門前雪相差甚遠。
我在這裡待了兩個月,終於漸漸習慣這裡盛夏的熱情還有猖獗的蚊子,終於可以只用著一支電風扇就度過一個下午,但我最喜歡的還是待在房間裡看著那些過去歲月留下的痕跡。那是三樓的一間空房,奶奶以前跟爺爺的房間,許久沒有人居住,但是房間裡的擺設都還維持在爺爺生前的樣貌。奶奶說她現在一個人住不了那麼大的房間,一個人待在那房間裡,孤寂就像漲潮一樣緩慢而堅定地席捲上身,多待一秒都讓人難以承受。但是我喜歡這間空房,深埋在寂寞底下的是挑揀後的逝水年華,泛著淡黃色的回憶在這裡顧自地散發出微光。
「央央!」奶奶在樓下喊我,「沒事就出去走走啊,不要老待在家,現在早就不興大門不出、二門不邁了啦。」
「喔,好啦,我下午就出去啦。」我下樓咬了一片剛烤好的吐司,上面塗了我最愛的花生醬,隨手又端一杯牛奶,走回三樓的空房。 房間裡有一扇落地窗,窗戶外的陽台爬滿了藤蔓,幾株牽牛花從密密麻麻的叢草裡長出來,迎著早晨的陽光散發出希望的味道,落地窗旁的一張搖椅兀自搖晃,晃出一片城市早晨的幽靜,這房間有一股民國初年奢華後遺留下來的紅塵頹敗感。
我喜歡在這個房間裡尋寶,在這裡翻出的任何東西都能讓我激動好一陣子。一張日據時期留下的戶口名簿,上面一個不知道幾輩以前的先祖,名字下面寫了「纏足」、一只斷成兩半的玉鐲子、一張紅紙褪成淺粉的囍字……越挖出古董,就越激發我的興致,興致一高我又繼續挖掘。 不小心,在一陣翻箱倒櫃中腳底打了滑,我往後一倒,撞上身後的木櫃,木櫃上的擺設嘩啦啦地掉落一地。我從散落滿地的雜物堆裡站起來,揉揉撞疼的後背,四周飛揚的灰塵讓我打了幾個噴嚏,忽然有光芒閃爍進眼簾,我從地上拎起光芒的來源,那是一串翡翠的耳墜子,仔細擦去它周身的灰塵,久遠的年歲絲毫沒有減損它的光輝,略微暗沉的綠色更顯出耳墜子的優雅端莊。
「阿央,你在幹嘛啊?」我猛地回頭,物品掉落的聲響驚動了樓下的奶奶,她站在房門口往內瞧。
「啊,那個,沒事啦、沒事啦,只是東西掉了而已。」在我身後那一地的杯盤狼藉實在是不好被奶奶看見,畢竟這個房間是她的回憶。看見奶奶欲往內走,我趕忙堵到門口,「沒事啦、沒事啦!你不用進來沒關係啦!」恰巧餘光瞥見手中的那一串耳墜子,我把耳墜子拎到奶奶眼前,「啊,阿嬤你看,我找到了這個!」 奶奶止住了往房內的步伐,捏起那一串耳墜子,「這個耳墜子……」
「對啊、對啊,我在櫃子上找到的!」我趕緊關上身後的房門,「阿嬤我們去客廳啦,不要站在這裡,很熱耶!客廳有電風扇,大台的,比較涼快啦!」
「央央……」
「嗯?什麼什麼?」我拉著阿嬤往樓下走,「走啦、走啦,我們去客廳啦!」
「嗯……」
段四
阿嬤軟綿綿地靠在沙發椅背上,目不轉睛直盯著她手裡的翡翠墜子,她的專注讓我訝異,「阿嬤……」
「央央,你聽過新婦仔嗎?」
自古以來,中國就有一種婚姻的習俗,是將未成年的女孩送養或賣到另一個家庭,在另一個家庭裡長大,長大以後嫁給他們的兒子。這些女孩就被稱為「新婦仔」,江南地區則喚「童養媳」,雖然稱呼不同,說的其實是同樣的悲哀。
奶奶就是別人口中的「新婦仔」。
奶奶的老家在中國的農村,家裡特別窮,吃飽穿暖都是問題,偏偏那時候又遇上日本跟共軍交互的打擊,戰爭一場接著一場,這裡歇了那裡烽火又起,全不給人喘息的機會。
「你想聽故事嗎?」阿嬤把耳墜子遞給我,開始訴說一段那年深埋在厚重塵土之下、帶著火燒火燎味道的故事……
那是一個艷陽天,但是炙熱的太陽照不清我心中的陰霾,我斜躺在牛車上,任由酷熱的陽光打在身上,身旁是一個小包袱,裡面寥寥幾件破舊的衣服還有母親大早起來燒的幾塊餅。我的小小身子因為長期營養不良,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了兩歲,我隨著崎嶇的路面顛簸,小包也顫巍巍地抖顫。 我看過很多人在這個時候都會大哭,但是我偏不哭,沒有什麼好哭的,就當是搬了家、重新投了一次胎罷了。
我是家裡最長的女兒,下頭還有兩個弟弟,一個五歲、一個三歲,我下田勞作的時候,五歲的弟弟也會陪著我一起幫忙,但僅有五歲的年幼孩童能幫些甚麼呢?弟弟們都不過還是嗷嗷待哺的年紀。說是幫忙還不如說是陪伴來的更為貼切。
從我記事以來,中國就一直在打仗,或者說是在被打,整個中國都是煙霧瀰漫,沉溺在一股戰爭的低氣壓之下。也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無止盡的戰爭,反正國家的事情怎樣也落不到我頭上來,我那時每天最大的願望,不過就是能夠躺在屋內的通鋪好好睡上一場日上三竿的覺。
我還記得父親長滿厚繭的手足還有母親日漸消瘦的身軀,看著他們每天都為了生計煩惱、為了生活而深鎖的眉心,那時候跟我同一個村的女孩都被賣去做童養媳了,我想那大概也會是我的命運,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來。
當年母親將所有的財產換成了金子,「雖然現在的日子看似和平,我們還是過著平常的生活,該幹嘛就幹嘛,可是誰又說得準下一刻的事情?」 我站著,母親坐著。我這才發現,曾經是母親最引以為傲的烏亮青絲,現在變得滿是斑白;又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母親的聲音變得如此嘶啞?我記憶中的母親,那個黃鶯出谷一般,時不時哼唱兩句的母親在不知不覺中在柴米油鹽的煩憂中消逝了。
「要是村子裡突然闖進來一輛裝甲車,還是有一堆人拿著步槍衝進來,那個時候我們連逃都來不及啊!」母親說,「等到了那種地步,錢幣、紙鈔的,哪裡還派得上用場?還不全成了廢物。倒不如換了金子,心裡踏實些。」
我看著母親的臉龐,母親的臉啊,曾經是那麼精緻細膩。小時候最喜歡摸著母親的臉,感受她細膩的皮膚,還有她滿滿的愛意,從笑彎了的眼睛跟嘴角裡溢出來。母親當初被街坊鄰居稱羨的一張臉,如今卻已經染上了風霜、染上歲月無情的痕跡,她的眼角深深地刻上無數條魚尾紋,還有眉間的皺紋,濃得化不開的擔憂全寫在她臉上,擔憂我們、擔憂戰爭、擔憂生活。我多麼希望能讓她的眉頭舒展開來,讓她再變回我記憶裡的模樣。
段五
我害怕的命運終於還是來了。
那一天整個屋子異常的安靜,我走進屋裡,發現連父親母親的對話都被刻意壓低了聲音,我從隔開睡鋪的布簾上看見人影晃動,我躡手躡腳地走過去,將耳朵貼上布簾。
「……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啊……」父親的聲音傳來,晦暗不明一如我的未來。
「我知道啊……」然後是母親帶著哭音的沙啞。
「那妳就快別哭了……」父親無奈的說。
「但是我傷心啊,那是我的囡呀,才十二歲,都還沒長開的囡呀……」母親低低的哭泣,幾乎要泣不成聲,「我的囡呀竟然要去當別人家的新婦仔……」
剩下的就是母親停止不下的哭泣聲,還有父親不停的耐心安慰。我默默地退開,離開屋子以後我坐在屋子前面的泥地上,看著蔚藍的天空,我好想變成一隻鳥,向鳥兒那樣無憂無慮的高飛。
晚上的時候,我可以感覺到屋子瀰漫的低氣壓,我想著他們什麼時候要告訴我,關於我要成為新婦仔的這件事情。終於,父親清清喉嚨,「囡呀,等下先讓弟弟們去洗澡,我們有話要跟妳說。」
「爸爸、爸爸,你們是不是偷偷藏了糖果要給姊姊?不行、不行,我也要吃糖、吃糖。」五歲的弟弟聽了這句話,歪著頭天真的說。 「糖糖、糖糖。」最小的弟弟聽見有糖果,流著口水含糊不清的叫喊。
「好好好,我們先去洗澡,洗完就有糖吃了,好不好?」爸爸好容易哄走兩個弟弟。
剩下母親欲言又止看著我,「囡呀……」母親拉著我的手,「囡呀,我跟你爸爸啊,幫你找了一戶好人家,他們家裡可比我們家有錢多了,以後你去了那裡,就不用擔心吃不飽、穿不暖……」她擦掉眼角的淚水,「說不定、說不定,他們還能送你去讀書呢!隔壁的那個阿姊妳知道吧,她現在可好了,還識字,是人人稱羨的女學生呢!你不是最想要習字了嗎?以前我們家裡沒有錢讓你學習,說不定到了新人家,你就能學習了呢!」母親邊說,豆大的淚珠就順著臉頰滑下來,在她臉上淌成一條晶瑩剔透的小溪。
「嗯。媽妳不要哭啦,我會很好的啦,妳不是都跟我說農村的小孩命大嘛!而且我以後也是要當女學生的呢!」我帶著哭音抹去母親臉頰上的淚水。 「乖囡呀、我的乖囡呀……」
終於壓抑不住悲傷,我們緊緊相擁,我想要記住母親的體溫、她的氣息、還有她的聲音、她的一切。
段六
「二弟,」我叫住在屋外玩耍的弟弟,「你過來一下。」
二弟聽見我喚他,一蹦一跳的跑過來,「阿姊、阿姊,妳看。」他舉起他的滿手泥巴,像炫耀什麼寶貝一樣給我看。 「好髒喔你,等下記得把手洗乾淨,不要弄髒床鋪,不然你又要挨打了。」
「好啦,我知道了啦,媽媽兇起來太可怕了。」看見他吐舌頭的可愛模樣,我忍不住笑出來。
「二弟,我跟你說喔,阿姊有事情要離開家裡,就變成你最大了,所以你要好好照顧阿弟喔!還有不可以調皮搗蛋、不可以惹媽媽生氣喔,不然閻王爺要來抓你呢!知道不知道?你如果都乖乖的,阿姊就帶很多很多糖果回來給你吃。」
「好啊、好啊!我跟你說,我最乖了!才不會調皮搗蛋呢!阿姊你要記得帶糖果回家喔!要帶很多很多糖果回家喔!」
「那當然。」
「阿姊我們拉勾,說謊的是小狗!」
「好!」
對不起,二弟,阿姊這次只能當小狗了。
「小姑娘?到了呢,快下來呀!」
跳下牛車,四周環顧了一圈,發現我的新家比我原本住的地方大的多了,我直看得傻了,以前都生活在農村裡,沒有出過村子,還是第一次看見這麼大的房子。
「快過來呀!」一個大嬸叫我,「你叫甚麼名字呀?」
「我、我叫招弟。」
「姊姊……」突然衣角被人拉住,我回頭一瞧,原來是一個小男孩,跟二弟差不多的年紀,應該也是四五歲。
「喲,你在這裡呀。」他疼愛地搓揉男孩的頭髮,「招弟呀,這就是你以後的小丈夫了啊。你以後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要照顧他,換尿布、洗澡、吃飯、睡覺,這些都是你要負責。另外,家裡的雜務你也要幫著做。聽懂了嗎?」我呆呆地點了點頭。「懂的話就快幹活吧。」 我看著小男孩,男孩吃吃地笑著,我實在還不能適應這樣一個跟二弟一樣年紀的人以後就是我的丈夫了。大嬸留下我跟小男孩就離開了,剩下我跟小男孩兩個乾瞪眼。
我在小男孩面前蹲下來,仰起脖子看他,「你以後就叫我阿姊好了。我叫你阿弟。」
「阿姊。」小男孩傻呼呼地叫了一句。
「好乖。」
我跟阿弟的日子過得很快樂,雖然除了照顧阿弟,還要幫忙家裡的各種雜務,但是阿弟是一個很愛笑的小男孩,我看著他就像看到自己的親弟弟,再怎麼樣辛苦的做活都覺得津津有味。我每天就拉著阿弟到河邊,我洗衣服、搓尿布的時候,他就坐在河邊聽我給他講故事,大部分講的是我以前在農村裡發生的故事,他也愛聽。「阿姊,我也想去村鎮玩。」他癡癡地聽完以後總是這樣說。
「好哇,等阿弟長大了,阿姊就帶你去玩。」
這樣的日子過得倒也快,我發現阿弟跟我越來越親近,當阿弟的母親發現阿弟喜歡黏著我以後,我要做的雜物就變少了,「你就專心照顧他就好了。」所以我更是變著法子地討他愉快。我教他游水、給他戴花圈、做糕點、買糖果。無所不用其極。但我也確實是真心喜歡這個阿弟的,我喜歡這個小孩,我想帶他去我的農村,帶他認識我的父母、還有我的兩個弟弟。跟阿弟在一起的時候,就讓我想到父親跟母親、想到家裡的兩個弟弟,讓我覺得我離他們還不至於那麼遙遠;覺得我還是在家裡、還是在帶著二弟跟阿弟。
照顧阿弟的日子不知不覺間過了兩年,這一年,家裡附近來了一群學生,有男有女,男學生一個一個意氣風發,散發著讀書人的儒雅氣質,像極了母親跟我說的〈西廂記〉裡面的書生。那些女學生也美,短頭髮梳得整整齊齊的乖巧地貼在頭上、長頭髮的就扎成一個辮子,走路的時候長辮子就在背後甩呀甩的,我摸摸自己的頭髮,毛毛躁躁、亂七八糟完全就是一個鄉村土姑娘的模樣,這是我第一次不希望我是一個農村姑娘。
回家以後,我照著女學生的模樣,給自己好好整理了一回,也學著她們綁了一條辮子,阿弟特別喜歡玩我的辮子,他說像是他愛吃的麻花捲。那些學生常常聚在一起學習,當他們學習的時候我就買糖果塞給阿弟,然後帶著阿弟,阿弟專心地吃著糖,我就偷偷躲在牆角偷聽他們讀書,去的時間久了,連阿弟都學會了幾個大字。
阿弟的母親以為是我會習字,交給阿弟的,對我大大的誇獎了一番,他們覺得女孩子會讀書很不容易,不應該就這樣荒廢掉,於是,他們做了一個決定──讓我帶著阿弟去跟那些學生們一起學習。
我終於也是女學生了。
我開始跟著大家一起讀書,這種感覺特別好,我跟著那些學生習了不少字,也聽了很多新思想,才讓我知道原來女生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獨當一面,不用依賴丈夫生活。這些想法深深地衝擊我,就好像一個在森林裡行走多年的人,森林裡古木參天,霧濛濛的一片,陽光也照不進來,走在裡面什麼都看不清楚,就在這個時候突然有人領著我走到了出口,走出生活多年的森林,才發現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遼闊。但是這些想法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更不用說告訴阿弟家的人,要是阿弟的母親知道我都學了什麼,肯定立刻就不准我跟阿弟再去了。幸好阿弟還小,聽不懂這些「驚世駭俗」的道理,小孩子喜歡說一些她學到的東西,我買幾顆糖給他,「你回去以後只能說那些書上教的,其他都不能亂說。」在糖果的威力之下,倒也不怕他回去多嘴。
段七
去的久了,也跟大家熟識,我漸漸地跟一個男學生好上了,他一開始其實很不待見我,覺得我只是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土包子,他後來告訴我,是我認真的態度改變了他的想法,他說我什麼不懂就問,也不在乎別人會不會嘲笑自己,他很佩服我的勇敢。他開始教我學習,只要哪裡不懂他就會耐心地說給我聽,每當這個時候,阿弟就在旁邊自顧自地玩耍,他只當我是因為家裡沒人,所以要帶著弟弟一起學習,自然從來沒想過阿弟是我丈夫。他也對阿弟好,阿弟很喜歡他。
因為他,我的學習生活多了一點淡淡的粉紅,但是我不能告訴任何人,連阿弟也不能,這是只屬於我的秘密。他帶我去看了很多地方,自然阿弟回回都跟著,阿弟的媽媽也沒有起過疑心。我知道他喜歡我,我也喜歡他,但是我們誰也沒有說破,他還是給我上課,給我教我不會的東西。我們享受這樣的曖昧,這種感覺特別好。
又過了五年,這一年阿弟的母親決定讓我跟阿弟「圓房」,我知道「圓房」是什麼,畢竟我也算是一個女學生,但是我不想,阿弟就像是我的親弟弟,我沒辦法想像,這實在太奇怪了。我不能拒絕,儘管我內心女學生的靈魂不斷呼喊叫囂著要我抵抗,但是我身為一個童養媳卻是不爭的事實,他們養我就是因為這一天,如果我不服,我看過因為不想「圓房」而抵抗的人,後果很慘,我好不容易在這個家裡過得很好,我沒有必要、也不想打破這個平衡。
我以為我的人生幾乎就要在這裡劃下終點了。跟阿弟圓房、不再去學習、生一個阿弟的兒子、帶兒子,最後慢慢地變老,或許再給阿弟的兒子買一個童養媳,就想阿弟的母那樣,他的母親也是童養媳,童養媳就像是一個無止盡的因果循環,沒有人有能力可以阻止。
就在這一年,一場戰爭改變我的人生。
那時候上海跟南京大學的學生主張著「反飢餓,反內戰」。《新華日報》每天登著中共軍隊勝利的戰報,又將中共俘虜的國軍公布在報紙上讓家屬認領。在節節敗退之後,蔣公最後終於決定退守台灣。阿弟的家人也整理了所有的行李要去台灣,原本預定的「圓房」也不了了之。「生活都有問題了,誰還管什麼圓不圓房啊!」阿弟的家人這樣說。他們本來不打算帶我去的,畢竟多一個人就要多一張船票,到台灣還不知道未來,多一個人等於就是多一個麻煩的包袱。「不行、不行,阿姊不一起去我就不去。」結果是阿弟的一句話救了我。我何德何能啊。「阿姊,妳就是我的阿姊,阿弟怎麼可能把阿姊一個人丟下來。」我才發現,原來我們的關係早就超越了阿弟父母親預想的童養媳跟小丈夫,而在不知不覺間昇華成更穩固的親情。
臺灣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以前的我,只從別人的對話裡聽說過幾次,他們都說台灣是一塊人們夢想中的淨土,沒有煩惱、沒有戰爭、所有人豐衣足食。「妳有聽過桃花源嗎?那裡就是一個十足的桃花源境地。」
我們打包好所有行囊,搭上船,隨著許多搶到船票的逃難的人一起,海上風雨飄搖,船在大海上像一個失去方向只能隨波逐流的落葉,但是再怎麼樣搖晃的船身,都遠沒有戰爭的中國讓我們害怕。「只要到了台灣,我們就安全了」,大概是這樣的信念堅持著我們這一群人。
終於到了岸邊,船上所有人爭先恐後地下船,人潮蜂擁向外擠,我原本緊握著阿弟的手在人潮推擠之中竟然空了──我跟阿弟他們一家人竟然在剛到台灣的瞬間就走散了。四周滿滿地都是人,我在人群中大聲的叫喊著阿弟的名字,一次又一次,叫到嗓子都啞了。我想要站在原地等著阿弟他們家的人來尋我,可是後面不斷蜂擁的人群把我往前推,我的腳幾乎碰不到地板、幾乎是人群夾著我往前移動,我一個人的力量根本抵擋不了,只好順著人群,等到終於停下來的時候,我根本不知道身在何方,更不用說回頭再去找阿弟了。
段八
奶奶停下來喝了一口茶,「我就是這樣來台灣的。」
「阿嬤……」我被她的故事震懾住了,我的奶奶,就想大部分女人一樣,生兒育女、養家活口的平凡女人,竟然還有著這樣一段故事,「我都不知道……」
「那當然,因為我從來沒告訴過你啊。」她和藹地笑笑,「其實啊,我的故事沒有什麼特別的,那時候的人幾乎都是這樣過來的,大家都有各自的艱辛啊……」
「那後來呢?」
「後來啊……我終於踏在這塊土地上,也生活了幾十年,我並不覺得像他們說的那樣,台灣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桃花源。但是現在這樣就已經很好了,做人要知足,這個道理我還是懂得。」
奶奶說她最幸運的地方大概就在於她恰好碰上了戰爭。
因為戰爭離開了原本的家、離開後來的新家、離開中國、也離開她的童養媳人生。
她沒有再去找她的阿弟,反正找到了還得回去當童養媳,既然她現在識字了,而且許多事情她都會,那她一定有辦法自己活下去。一開始當然是艱辛的,一個女人,要在完全陌生的土地生活,她被騙過、也因為沒有錢,被人從租來的屋子裡扔出來過、也曾經露宿街頭,但是奶奶說,她並不覺得辛苦,或者是說她樂在其中,因為這是他長這麼大,第一次享有完全的自由,以前的她是被束縛的,小時候被家裡的弟弟們、被她身為「女兒」的身分束縛;當了童養媳又被另一個身分、另一個家庭束縛。現在她就站在台灣的土地上,是完完全全自由的一個人,不用在意別人的目光,也沒有那麼多身不由己,這是他第一次為了自己生活,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樂跟激動。 她後來在台灣結婚生子,過著雖然不富裕但是安定的小康生活。她很滿足。
後來曾有個老鄉來找過奶奶,老鄉是奶奶小時候住在她家隔壁的大嬸,家裡人因為從軍打仗都死光了,只剩下大嬸一個人,大嬸對奶奶一家極好,常常接濟他們,「反正我老太婆一個也吃不了這麼多」,大嬸總是這樣回應奶奶一家人的感激。大嬸告訴奶奶,奶奶的二弟從了軍,也隨著軍隊來到台灣。前不久開放探親,二弟回去過老家一次,那時候大嬸剛好也回農村裡找故人,碰巧遇上弟弟回去那幾天。大嬸說奶奶的弟弟也沒留下聯絡方式,打了聲招呼就離開了,現在也不知道在哪裡。
「妳的那些親戚啊,還真不是個東西!瞧著妳弟弟是從台灣來的,喲!竟然還想著和妳弟弟要錢,他們可真是有臉呢!這如意算盤打得可真夠響的!」她冷笑地跟奶奶說。「不過啊,妳弟弟那還真是一個有骨氣的、鐵錚錚的男子漢!果然是待過軍隊的,不一樣呢!一點親戚情面也不顧,愣是不借半毛。要我說啊,他這樣做就對了,他要是敢借錢,看我還不打斷他的腿!」
大嬸後來也過世了,之後就再也沒有故人來找奶奶。奶奶也沒有在台灣見過她的二弟,她也不抱希望,想著都過這麼久大約也不可能再見了。至於最小的弟弟,奶奶說她是真不知道了,大嬸聽村裡人說,他後來也投了軍,死在某一場戰爭裡;也有人說,他是在戰爭中染病,病死了。不管如何都是死了。在奶奶知道這個消息的那一天,她買了一包糖果,供在佛桌上,點了一炷香拜上一拜,「我最小的弟弟最喜歡吃糖了,可惜我從來沒買過糖給他。」
人終歸一死,真相到底是什麼似乎也不那麼重要了。那些過往的歲月,對於奶奶而言,就像是上一輩子的事情,一切都是那麼遙遠。 「阿嬤,那這個故事跟這串耳墜子有什麼關係嗎?」
「妳不說我都忘了,這個耳墜子啊,是阿嬤的媽媽當初在阿嬤離開家裡,去給別人家當童養媳的那一天偷塞給我的。我平常可不敢戴,都把它好好地放在衣服內的兜裡,後來我要找就到找不到了,還以為被我弄丟了,傷心了好久。」她溫柔地撫摸手中的耳墜子,像是撫摸一生的摯愛,但是我知道,這串耳墜子的意義,遠不是摯愛可以解釋,這是奶奶前半生的回憶,不管是在農村裡跟家人在一起的時候也好、給人當童養媳也好、跟那些學生一起讀書的時候也好、跟男學生好上的時候也好……「對了,阿嬤,那個男學生呢?你們後來沒有在一起嗎?」 「當然沒有啊。我後來的家人對我很好,而且我怎麼說也是已經嫁人了,嫁給了後來的阿弟。也不知道他後來怎麼樣了,逃難那之後就再也沒有聯絡了,不知道他過得好不好……」
「好可惜啊。」我嘆息。
「有什麼好可惜的,一切都是命。再說了,我跟他在一起的話哪裡還會有妳啊。」奶奶把耳墜子塞進我手裡,「央央,妳喜歡這個耳墜子嗎?阿嬤把他送給妳,妳覺得好不好?」
「喜歡呀,可是,這是阿嬤唯一剩下的紀念了。如果我把它拿走了,阿嬤以後就沒有東西可以懷念了。」
「怎麼會呢,」奶奶戳戳我的腦袋,「阿嬤的紀念都在阿嬤的這裡,誰也拿不走。而且阿嬤現在也用不上耳墜子了,就給妳吧,妳幫阿嬤好好保管它。」
段九
我後來告訴夏倪茹這段烽火之下故事。她說,「這不就像妳看的書嗎?那本什麼維特的?」
「妳是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哪裡像啊?」
「就是你最喜歡的,維特最後寫給綠蒂的信啊,不是說什麼『這並非絕望,而是對自己的決心深信不疑』,我覺得這就很有妳阿嬤的精神啊,不沉溺在自己的過去,也沒有因為只有她自己一個人在台灣而感到絕望,相信她可以活得很好,最後還能在台灣找到自己的幸福。真的超厲害的啊,我的話應該早就餓死街頭了吧。」
「是滿像的啦。可是,這封信的重點不是這個……」我無語。
「咦?不是嗎?」
「……」
段十
幾個月以後,奶奶得了失智症,有時候連我們她都忘記是誰,爸爸說其實奶奶之前就被確診了,只是症狀不明顯。我想那一次她告訴我的故事,大約算是一種迴光返照吧,又或許奶奶一直支撐著不發病,就是想將她前半生的回憶告訴願意聽她說的子孫。對奶奶而言,那些過去的歲月真的就永遠封存在她的記憶裡了,在她把耳墜子遞給我的瞬間,也是將她的記憶一併交付了。
夏倪茹後來告訴我,在我大二那年男朋友發生的意外,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我。那時候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冷戰了好幾個星期,他當時騎著機車是想要給我買一個戒指,他要跟我道歉,他說他畢業一找到工作就要跟我結婚,騎著騎著,他在路邊看見我的背影,他急切地想要把戒指送給我,一不小心他打滑了,又剛好這麼湊巧一輛車從後面開過。而我並不知道他當時躺在馬路上,生命垂危。這些都是他爸媽告訴夏倪茹的,但是他們不要夏倪茹讓我知道,他們不想我內疚。
「但是我想跟妳說,他到底有多愛妳。」夏倪茹說。
「嗯,謝謝妳。」
我後來想,世界上的事情似乎真的像維特寫的那一封信,很多事情都是求之不得的,有的人會因為痛苦而寧願死去,但有的人卻能夠舔著傷口活下來,並沒有誰比誰更高尚,這些都不過是每個人的選擇。死去的不一定比較愚蠢,因為他們會用另一種方式存活下來,那是在心裡誰也奪不走的回憶;活著的也不一定美好,那些傷口在夜深人靜時總會隱隱作痛,提醒曾經的苦痛。
我會帶著奶奶的回憶,還有我自己的悲傷,努力的活下去,這些過去並不是負擔、不是痛苦,而是支撐我的力量,讓我知道曾經有一個人,他這麼愛我。還有奶奶的故事、她的耳墜子,現在則是我的耳墜子,在我的右耳閃爍著那些逝去年華的餘輝。
-完-